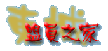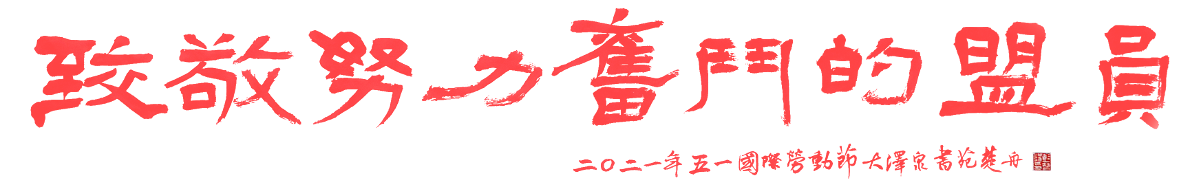论道大戏剧 立身大先生——记中央戏剧学院麻国钧教授的戏剧人生
麻国钧先生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过三届民盟中戏支部的主委,是第一届民盟东城区区委委员。

早在2010年,麻先生的开门弟子、戏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蔡美云就曾撰写过《本土情怀 广博视野》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麻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麻国钧,吉林省吉林市人,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部优秀专家。任中央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戏剧学院院刊《戏剧》编委,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副会长及法人代表。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戏剧史论、中国古代文化学、东方戏剧。1995年至1996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聘请而出访日本,考察日本民俗艺能。曾多次出访韩国、印度、越南、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主要著作有《“行”与“停”的辨证——古典戏剧的流变与演剧形态》、《中国传统游戏大全》、《中国酒令大观》、《玉簪记评注》、《日本演剧史概论》(译校)、《日本民俗艺能》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目连戏特色十议》荣获“第三十五届田汉戏剧奖”理论一等奖。
在当代戏曲史论和戏曲文化研究中,麻国钧先生是不可忽略且建树颇丰的学者。迄今为止,麻国钧先生发表的论文超过百篇。作为首席专家,麻国钧先生主持并完成了众多重要的科研项目,如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傩戏与东亚古典戏剧比较研究”、院内科研项目“东亚传统演剧空间文化比较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东亚民俗演剧假面史论”,目前正在进行中。
在勤奋且瞩目的学术活动之外麻国钧先生还承担了诸多社会职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华戏曲》编委,中国傩戏学研究会顾问。2022年麻国钧先生被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聘为“学术研究部主任”,第一期聘期五年;2023年他接受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草的聘请,成为中国皮影艺术传承与创新研究院研究员,聘期五年。
得大师真传 承学术之道
说起来在我们中戏有一个习惯,导演、表演系一般称前辈老师都直呼其名,比如徐晓钟老师当了那么多年院长,大家还是尊其为“晓钟老师”,而戏文系则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尊德高望重的老师为“先生”。在中戏能称之为先生的一定都是“大家”,是大师级的学者,比如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家琇先生,戏剧理论家祝肇年先生等。
七十年代后期,麻国钧先生在戏文系做助教,讲授《剧本分析》、《中国戏曲》等课程。从那时起,他就追随著名戏剧理论家祝肇年先生,并深得祝先生厚爱和亲传:聆听祝先生讲授戏曲,与先生共同探讨学术问题,也常与先生彻夜长谈,谈诗论道,品评书画。可以说,麻国钧先生承袭了祝肇年先生在戏剧戏曲理论研究方面严谨的治学之道,并进一步发扬光大。1986年,麻国钧考上了戏文系在职硕士研究生,正式成为祝肇年先生的嫡传弟子,进一步研读中国古典戏曲史论。在跟随祝先生学习的几年里,他系统学习了中国戏曲史、中国戏曲理论、中国古典文学,阅读了大量古典戏曲剧本,研习大批古典文献,并对一些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撰写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国戏剧的发生》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发表在《戏剧》1989年第3、4 期。论文尝试用系统论的理论,结合民俗学、宗教学以及人类学的方法,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对中国史前戏剧的发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麻先生认为中国戏剧的发生与宗教祭祀有着直接关系,宗教祭祀直接孕育了早期戏剧的基本形态:从最初的娱神到最终的娱人,中国戏剧走过了几千年。他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是从“巫”、“优”到“演员”的演变,突破了王国维先生的“巫优说”,对20世纪80年代的戏曲理论研究有独到见解。
除此之外,麻国钧先生认为中国戏曲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剧本研究和文献研习上,而是要把戏剧看做一个立体的、文献与舞台演出并重的活的艺术,他更加强调舞台和演出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003年,他出版了《“行”与“停”的辩证——中国古典戏剧的流变与形态论》一书,从“流变考述篇”、“演出艺术篇”、“文本篇”三个方面对古典戏剧的流变和形态进行了勾勒,这是其学术研究的集大成者。此书着眼于东方戏剧视野,不仅对中国古典戏剧形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述,还兼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戏剧形态。书中指出,行进的祭礼及演出艺术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戏剧文化现象,即中国古典戏剧的发生与发展、古典戏剧的演出形态,都曾经极大地受惠于古老的行进祭礼、行进演艺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作者列举大量例证,论述行进演出艺术对文学剧本结构上的影响与制约。这本书建立起一个几乎全新的材料系统,辩证地论述了“行”与“停”的多层关系,在当今古典戏剧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此书被评为第八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追随祝先生深入研习,先生个人的品行、学养、爱好等,为麻国钧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以及为师为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他的深度思考和学术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作为学者,尤其是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戏剧戏曲研究,扎根本民族文化大地,潜心钻研非常重要,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文化人的清高智雅,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兼济天下,在中国以及世界戏剧文化的传承中做些利国利民的好事。麻国钧深谙其中的道理,他把对祝先生的敬重都倾注在对后学的教育教诲中。他常对名下的博士硕士生们讲起当年与祝先生“华山论道”的星夜对谈,讲述自己读书、田野考察、出国访学时的思考。他要求青年后学们做人做事要大气大度,讲团结,多奉献,互学互助。
近年,随着麻国钧先生自己年事渐高,他也变得善感,更加思旧,每念师恩就眼眶泛红。记得他的夫人淑云老师讲过一件小事。有一次,整理旧物时发现了祝先生的一封家书,麻先生居然手捧信笺掩面大哭,吓得夫人竟不敢贸然规劝。其实,我们都明白,麻先生至今仍旧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带领年轻的博士硕士在大戏剧观的统领下,在更广博的视野中研究中国戏剧戏曲以及东亚戏剧在文化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中的发展和嬗变,就是对恩师祝肇年先生的最好纪念。1998年,麻国钧先生牵头编选了《祝肇年戏曲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祝先生的遗稿内容丰富且繁杂,从整理誊写到校订出版,麻国钧先生用尽心思和精力。该书浓缩了祝先生毕生研究成果的精华,也为后学者研究祝肇年戏剧成就和研究中国戏曲提供了宝贵资料。

麻国钧(左)与恩公祝肇年先生(中)合影
戏剧研究需要传承与发展,麻国钧先生就是戏剧研究界杰出的继承者和传承人,是戏剧研究与教育领域广而博的杂家和大先生。而今,中戏人也习惯地称麻国钧老师为“麻先生”,他终于可以承学术之道,扬先生之名了,这既是对恩公最好的敬畏,也是对“大先生”最恰当的解读。麻国钧先生身体力行,让我们目睹到了中国戏曲戏剧研究与教育领域里大先生的风采。
赴田野考察 促教学鲜活
在麻先生眼中,做顶流戏剧学术研究既不单纯是戏曲史论研究,也非戏曲考据学研究,而是要走出一条独特的探索研究之路:开展田野考察或实地考察,促使教学研究更加鲜活有趣。就中国戏曲来说,要关照中国乡土文化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风民俗,关注那些至今还活着的早期艺术因子,以此为背景展开戏曲研究。为此,他和弟子们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看了很多至今仍然演出的民间祭祀戏剧,如河北固义村的打黄鬼、山西曲沃的扇鼓神谱、湖南湘西的民间祭祀演出等,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河北武安社火中的儿童竹马 秦腔《潞安州》
田野考察时,麻先生身背照相机健步如飞,像小伙子一样爬高下坡,比年轻人兴致还高,体力还强。他带着学生行走在乡镇农舍、田间地头,访遍寺庙宗祠,看农村土戏台,听老人说戏唱戏,看当地人表演地方戏,足迹遍布山西、河南、河北、江苏、湖南、贵州、江西、云南、内蒙古等地,甚至远至新疆。有一次拍照时不小心从高台上掉下来摔伤了腿,感染后高烧不退,他竟一直坚持回北京才住院。蔡美云老师去看望他,看着腿上的伤口,感觉很严重,麻先生却不以为意,还幽默地说这几块伤口的形状“好像七星伴月”……
傩与傩戏,既是宗教祭祀的产物,也是早期戏剧的形态在今天的流变。作为一种特殊的戏剧样式,它不仅保存了早期戏剧的很多可贵的特点,使我们尽可能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依稀看到远古时期祖先的戏剧样式,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对戏剧多样性研究和探求的可能性。学生在麻先生的课堂上,可以见到他通过田野考察带回来的各种鲜活的资料,通过那些原始形态的、偏远地区或物质文明并不发达的村落中那些虔诚而质朴的,只属于他们的宗教仪式和戏剧仪式的活动,让学生依稀可以触摸到远古艺术的灵魂,与古人一同体味心灵的受难与狂欢。为了让学生更形象地感知傩和傩戏,麻先生偶尔还会在课堂上伸展双臂,转动身形表演,甚至会不顾危险,站在椅子上进行展示。麻先生通过田野考察带给我们关于傩戏、皮影戏等中国戏曲的图片以及影像资料,是对中国民间戏剧研究的一种原生态式的补充。麻先生讲课声音宏亮,中气十足,时不时还穿插着手舞足蹈、寓教于乐的表演,生动形象、活泼有趣的教学展示,让戏曲教学情趣盎然,在如今PPT教案盛行天下的大学课堂上尤为弥足珍贵。

麻国钧先生为硕士生、博士生授课
再说实地考察。东亚戏剧的交流,比如日本戏剧的形态。麻先生1995-199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期间,实地考察和观摩了很多日本戏剧演出。包括日本古老的能乐、狂言、歌舞伎以及为数众多的民俗艺能,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演出资料,包括图片和录像,方便日后教学与研究使用。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东京都两大田游》、《泷山寺鬼祭》、《名闻遐迩的佛教哑剧:壬生狂言》、《日本的钟馗信仰·钟馗艺术与钟馗戏》、《日本的佛教地狱剧:鬼来迎》、《日本祭礼行事与民俗艺能总览》、《说鼓——鼓的神性及其在祭礼演艺中的体现》等,这些文章第一次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戏剧的见闻和对日本戏剧的思考,并发现了日本戏剧与中国戏剧相通的地方和相似的美学意义。

麻国钧先生书房一角
尽管日本戏剧与中国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文化上的渊源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时至今日,日本戏剧在中国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麻先生实地考察后撰写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了解日本戏剧发展诸多形态的渠道,所耗费的心血和艰辛汇聚其中。学生亦可在麻先生的课堂教学中窥见一斑,这种课堂看起来就很美很香,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热爱戏剧的学人近距离观赏和揣摩,仅此一点就让麻先生欣喜万分了。
为盟务奉献 做院长担责
麻先生于1997-2021年间先后担任民盟中戏支部的组织委员和主委,其中做主委13年,期间担任第一届民盟东城区区委委员。盟员们都很清楚,基层盟务工作都是兼职的,没有点奉献精神是无法在固守本职工作的同时做好盟务的。那时候麻先生正值事业上升期,学者出身的他,以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守土有责地扎扎实实做好支部和盟区委交付的工作。笔者之一作为当时支部的宣传委员有几件小事记忆犹新:一是自麻先生担任主委后,利用自身的学术影响力积极寻求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每年必定组织1-2次外出,全体盟员共同参加专题研讨活动,并邀请盟区委领导、中戏党委主要负责人莅临指导,有时还会联合东城区其他支部联合行动,盟务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坚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积极为学院内部的教育改革出谋划策,在学院统战工作中,民盟支部始终处在领先行列;每年定期带领或责成支部其他负责老师探望拜访资深老盟员,把组织的温暖带给为民盟组织建设做出贡献的老同志;积极培养物色提携盟务工作的后辈新人,真正发挥了民盟基层支部的作用。总之,民盟中戏支部就像盟员的家,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中戏民盟支部多次被民盟东城区委、民盟北京市委评选为东城区和北京市先进(优秀)支部。二是高效完成盟区委交办的工作,比如筹备组织当年的中秋晚会和新春年会。盟员耿光怡有幸成为组委会成员,她亲眼目睹过麻先生曾经细致地策划会议议程,邀请与会领导,组织节目排演,指导志愿者服务、审查节目单等,事必躬亲,亲临亲为,风风火火的。作为后辈,能在麻先生领导和指导下从事盟务工作确实学到很多,获益匪浅。

中戏民盟支部获奖证书以及支部活动的瞬间
麻先生的另一大贡献是从2001年到2006年做过5年中戏成教学院的副院长和院长,无论是主管教育教学还是负责全面工作,麻先生都一马当先。那几年麻先生一年四季常住成教学院,全年无休。从洽谈合作方筹建学院,到设计校园文化、招兵买马聘请员工,再到专业课程设计、招聘招生、开学典礼、审阅教案、教研听评课、实习实践、教学检查、期末汇报演出、毕业典礼、求职就业,连带后勤管理,食宿服务等,一应俱全,面面俱到。在专业设置上除了表演、导演、戏剧文学、舞台美术等传统专业外,根据市场需要也举办了如模特表演班等,为戏剧影视界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导演、演员、编剧、教师等。作为专家型的领导,他既懂专业又擅长管理,一竿子扎到底,把成教学院办得红红火火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学院戏剧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您能想象吗?麻先生正是在做成教学院院长期间,完成了上述诸多学术研究中的一部分,他真是拼啊!麻先生就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疯狂旋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生命的长度绝对不能用时间长短去衡量,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日日不息的奋斗中,无论是内卷还是躺平、摆烂,其实我们都是在痛并快乐中活着。
这就是麻国钧先生的戏剧人生。大幕还开着,人生看好谢幕还是不必谢幕?
补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麻国钧和麻淑云夫妇的热情帮助,民盟中戏支部主委姬沛教授鼎力支持,也得益于盟区委的协助。文内照片由麻先生和民盟支部提供。在此一并感谢。因时间和能力所限,尚不足以呈现麻国钧先生完满的戏剧人生。后辈仍需努力。
(作者:耿光怡 民盟北京市老龄委委员,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蔡美云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微信公众号 京盟享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