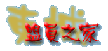季羡林:中国的历史会越来越长
最近几年来,我在个别文章中和一些座谈会上,发表了如题目所讲的这样一个观点。历史是本来已经形成了的东西,是不能再改变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连小学生都懂得的。我虽愚陋,还没有糊涂到连常识都不能了解的程度。
稍微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理解我的本意。我不过是说,历史确是已经完成了的东西;但是已经完成了的东西,并不等于我们都能够知道的东西。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东西本身确已完成而我们却还不了解。要举例子,俯拾即是。历史就是其中之一。
就拿中国史来说,对中国周以前的历史,我们眼前知道得不多,有的简直如蓬莱三山,隐入厚厚的一层神秘的云雾中。神话与历史事实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使人头昏目眩,分不清哪是历史真实,哪是神话传说。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甚至一个新的“千纪末”中,再过几年,一个崭新的世纪和千纪就要降临到人间,可我们对中国古代史了解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无须去查那些本子厚厚的《中国通史》之类的书籍以炫耀自己的渊博。我只须从几乎家喻户晓的《现代汉语词典》的附录中抄一点资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五帝”项目下写着“约前26世纪初——约前22世纪末至约前21世纪初”。表中排列着“五帝”的名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在“夏”这个项目下写着“约前22世纪末至前21世纪初——约前17世纪初”。时间上看上去没有矛盾,这一眼便可以看岀。但是稍微内行的人也能够知道,使用了几个“约”字,就说明,虽有数字,但仍在一团迷雾之中。
但是,我们仍然应当高兴。虽然仍有好多“约”,但是究竟有了数字。回忆70年前的20年代,顾颉刚先生等领导“古史辨派”风头正劲。他们勇于怀疑,钱玄同竟改名为“疑古玄同”,可见疑古风气之浓烈。顾先生有名的学说:大禹是一条虫,受到了鲁迅先生的讥讽。总之,“古史辨派”是不信有夏代的,更不用说唐虞了。当时,一般人承认,我们虽自称是文明古国,有记载的可靠的历史也不过三四千年,比起埃及和印度来,颇有点相形见绌了。
大可庆幸的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进展日益迅速,地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对最古的典籍的解释和理解,也有了进步。因此,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较前大有进步。我们已不能故步自封,坚持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唯一根源的观点。长江文化,其中最突出的是楚文化,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已大白于天下。原来古代南方的楚文化,其辉煌程度决不稍逊于黄河文化。我们读瑰丽神奇、幻想丰富的《楚辞》,爱其文章之雄伟诡奇,往往忘记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长期的文化积淀,能凭空陡然产生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来吗?连老子是楚人,也往往为我们所疏忽。不但荆楚一带是这样,连离北方黄河流域更遥远的云南、广东和属于今天华东地区的一些省份,考古发掘工作也揭露了一些新的为我们过去所不知的文化辉煌的例证,让我们的文化视野一下子为之恢弘、扩大。我们的目光再也不能局限于黄河流域了。
从地域上来说,情况是这个样子。从时间上来说,情况也差不多。同样是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迅速进展,当年被顾颉刚先生说成是一条虫的夏代的代表大禹,现在已经平反昭雪,恢复了人形。夏代确确实实存在过,这已被证明是一个历史事实了。那么,夏代以前的唐虞怎样呢?根据《古史辨》这一辆前车,我们有理由来预测,将来有朝一日,唐虞也会被证明是历史事实的。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古代神话传说都是历史事实,但是有些传说其中确蕴藏着历史事实,这一点早已被许多已经证明了的例子所证明了。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对古代史的了解比古人要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多。这看似奇怪,实则是事实。就拿我国的当代史来说吧,我们自己认为是亲身经历的事,其真相我们究竟能了解多少呢?恐怕50年后的人,要比我们今天了解得更多,更真实。我在上面用了“常识”一词,难道这不算是常识吗?
我说的这一番话,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一个有中等文化水平和理解水平的人,一读就能明白。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竟然不明白,而且不以为然。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又发表了上述的意见。这一位教授慢吞吞地说道:“在神话传说没有证明其中有历史事实之前,仍然只是神话传说。”说老实话,我当时确有点大吃一惊:一个搞历史的教授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竟然有这样的水平!他仿佛根本没注意到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和作用。如果历史倒退70年,倒退到20年代,当时大禹还是一条虫,我们这一位教授恐怕不会相信有夏代的存在,因为这还属于传说这个范畴。我和我们的意见是:既然夏代已从神话传说的迷雾中剥离岀来,为什么唐虞以至更古的朝代不能这样做呢?如果我们都像那位教授那样听任神话传说永远是神话传说,我们的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总之,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不能轻易地把神话当做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敢去碰神话传说。根据这个原则,根据“大禹是条虫”的前车之覆,所以我才提岀了中国历史会越来越长的说法。我相信,我的说法是实事求是的。
至于我们中国的历史究竟长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时间上的界限?那不是我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文章来源于群言杂志 1998年第1期 ,作者季羡林
作为时代的学术符号,季羡林先生为世人所敬仰。他不仅是一位学问大家,更是一位敦厚、亲切的长者。先生从1985年《群言》创刊之初便开始为杂志撰稿,直至他生病入院前,近20年的时间未曾间断。他曾说过:“为《群言》写点什么,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任务。”这是他对《群言》的厚爱与扶持。
2021年是季羡林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重温先生耄耋之年发表在《群言》的这篇文章,再次感知他孜孜以求、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这对当下“如何做学问”“如何研究历史”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